“让我感到欣慰的是,Belka Games愿意将利润分享给团队”
自去年11月以来,白俄罗斯工作室 Belka Games 由亚历山大·博格丹诺夫(Alexander Bogdanov)领导。在此之前,他在圣彼得堡创建了 Social Quantum、Game Insight 和 Playrix 的游戏部门。编辑 App2Top.ru 的亚历山大·塞门诺夫(Alexander Semenov)与博格丹诺夫谈了他的职业发展、X-Mercs 的开发及其转到 Belka Games 的原因。
我们通过 Skype 与亚历山大交谈。尽管今天是星期六,他却在办公室里。他桌上放着一个纸杯,里面盛着咖啡,他时不时地拿起来喝一口。
你今天是个完整的工作日吗?
是的。我喜欢我所做的事情,不觉得休息有什么意义。现在也不是休息的时候。
而且只有在周末,我才能安静地处理那些工作周忙乱中没有时间完成的任务。对我来说,这样的节奏是正常的。

亚历山大·博格丹诺夫
对自己不心疼吗?对工作的热爱可以理解,但有时力量是会耗尽的。
你说得对。确实存在过度疲劳的风险,所以需要知道分寸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,我保持自己习惯的节奏,并遵循一定的作息。
例如,如果我在周末工作,我会尽量不超过 5-6 个小时。首先,我会去健身房,然后再去办公室,最后一天结束时处理个人事务。如果自己逼得太紧,最后效率会下降,这对谁都没有好处。
我经历过 X-Mercs 的这个阶段。我们常常在 crunch 时在公司呆到凌晨两三点。我们觉得自己像英雄。但第二天就会遭遇工作上的宿醉,这对工作的影响是相当消极的。类似的超负荷工作可能会让你恢复一周。最令人沮丧的是,我们夜间的超额努力,最后还得重做。出错率很高,大家都很疲劳,还在赶工。最终,这种不规律的节奏带来的害处远超过短期的益处。
这很危险。那么在过度工作之前你是什么样的人呢?你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?我没记错的话,你来自阿尔汉格尔斯克,主修“银行业务”吗?
是的,几乎是这样的:我的第一学历涉及金融和普通管理。我参加的是免费的全日制学习,当然包括考试、全天在大学学习、拿到文凭,一切都是公平的。
在当时,这种教育看起来是清晰和稳定的,当时对管理者和银行员工的需求很大,这些机构刚刚开始建立。
这段教育让我明白了我大学毕业后要做什么。这一点非常重要,尤其是在阿尔汉格尔斯克。
而游戏开发则显得非常遥远——就像是在美国和欧洲发生的事,绝对不会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。
然而,从小我就很喜欢玩游戏。我开始玩的是 DM 和 ZX Spectrum。我不记得当时我有多大,但我首次有意识的游戏体验正是通过这些游戏获得的。Dendy、Sega 和 NES 是后来的事。
从那时起,游戏对我来说有部分收藏的性质。我努力玩所有能玩的游戏,并确保从头到尾都通关。我买了很多游戏,每一款游戏都投入精力去体验。对此我非常感兴趣。因此,我的学习成绩受到了一定影响(不过我从未是个优秀学生)。可以说,游戏那时已经是我的热情所在。
后来,俄罗斯开始出现第一台个人电脑。在我的朋友中,我是最早拥有个人电脑的人之一。要感谢我的父母。借助它,我看到了许多新游戏,包括传奇作品 Doom,这是第一人称视角的首批伪三维射击游戏之一。它让我惊讶不已,以至于我几天都不离开电脑屏幕。
但是,你第一专业仍然选择了其他领域。你是怎么回归到游戏的?这是在毕业前还是毕业后?
这一切发生在大学四、五年级的时候。我得到了一个 3ds Max 的光盘。那时它还没有称为 Autodesk,只是叫做 3D Studio MAX 或 Discreet 3dsmax。通过它,我了解了三维建模,开始创建模型,进行纹理处理,学习动画、渲染和粒子系统。
在此之前,你有过放弃玩游戏的时刻吗?就像说,长大了,不玩游戏了。
我从未停止玩游戏,但由于学习和我开始认真参加运动,我的时间变得紧张。部分因为 3ds Max,我重新找回了这份热情。
之前,我只尝试过手绘。但效果并不好。而在这里我可以直接做角色并为其准备纹理,给它赋予动作。这是非常棒的。
于是我开始制作自己的动画影片,进行剪辑,同时学会了 Premiere,并意识到自己的教育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。这在第五年时彻底确定下来。
我们有一个实习。我们被分配到各家公司和银行。我也被分配了进去。我在银行的工作非常不喜欢。我对银行职员没有任何偏见,但这绝对不是一个创造性的职业。至少在我所在的那个地方:信用部,全是日常琐事、纸张和不断的协调。
最初我忍受这份工作,因为它相对稳定,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很有声望。 但有一天我睡过头了。匆匆忙忙地准备时,忘了系上领带。银行没让我进去。人家说:对不起,朋友,我们是银行,有严格的着装规范,没领带是不让进的。
结果,我下定决心,不想再忍受这种形式主义和日复一日的琐事。我完全转向了自己的爱好——三维建模。于是我参加了“信息技术”方向的再教育。他所在的大学——波摩尔国立大学——提供这样的机会。
我在那里学习了一年,带着两个文凭离开Alma-mater——一个是学士学位,另一个是在IT方面的继续教育。
接着我试过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做所有能做的工作。在那个时期,正是视频广告、3D、特效、电视片头的高峰。我做了视频广告、3D 和特效,同时开了一家网吧,举办比赛。其中一部分是玩 Quake 3,我非常喜欢这个游戏。
我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待了一年,然后意识到自己做得不对。我想从事的是游戏。因此,我在 job.ru 上传了我的简历。

波摩尔国立大学
你申请了什么职位?
简历是 3D 建模师的。我投递后,惊讶地发现这个职业非常抢手。来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工作邀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。
后来我才意识到,当时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巨大。那时一切才刚开始。没有足够的模型师、游戏设计师和程序员。
当时甚至没有任何机构提供这样的课程。大家都是自学成才。
你为什么选择圣彼得堡?
当时我有一个选择——要么莫斯科,要么圣彼得堡。
圣彼得堡有点像阿尔汉格尔斯克。这也是一个港口城市。此外,在圣彼得堡我有朋友,对我来说更喜欢这个城市——它更安静,更从容。
我来到这里,租了一间房,然后一切就开始了。
第一家公司是游戏公司吗?
是的。我被 Kenjitsu 这家公司邀请。它是 Nikitova 的一个分支,主要专注于外包。它面向主要的西方客户,我们曾经与他们合作过一些项目,为 Electronic Arts 提供服务。
圣彼得堡的 Nikitova 分公司由伊万·特卡钦科(Ivan Tkachenko)领导 [后来成立了 Signus Labs,现在在美国初创公司 Cider Corp 工作,——编辑注]。正是他让我进入了游戏行业。
当时你也进入了艺术学院。是要求你去的,还是你自己意识到缺少传统教育?
我在 Kenjitsu 工作时,成为了一名三维艺术家,我很快意识到,在做有机体时,单靠移动多边形和展开是远远不够的。必须对比例、光、色和解剖有基本认识。没有这些,刚开始的我很难适应。举例来说,在我角色的手臂有些奇怪,肘部不在合适的位置,腿也不对。当涉及到面部工作时尤其会遇到很多问题。
我的同事们看到我在这方面的挣扎,并建议我参加艺术学院的夜间绘画课程。那里有一些想要进入艺术学院的学生。我在那学习了将近一年。得益于这些课程,我的世界观发生了第一次重大改变。完成这些课程后,我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周围的世界。
这种改变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?
我开始能在所有事物中察觉这些比例变化。我能立即理解哪个物体更近,哪个更远,什么在光照下,什么在阴影中。我的物体感知方式完全改变了。
我在课程中学习了从耳朵到头顶的经典雕塑课程。我们在课程上只画了鼻子超过一个月。并不是开玩笑。我每周要去上三次课,坐着画,然后不断修正。
我想建议所有搞三维图形的人去参加类似的课程,尤其是那些不会手绘的人。首先,这对纹理处理非常有帮助。其次,任何与学院理论相关的课程会极大地重塑一个人的世界观。
你是如何从建模师转变为项目经理 (PM) 的?
我一直把自己视为热情而有野心的人。那时我的野心与“我什么都知道”这种性格特质并存。大约在 Kenjitsu 工作了半年到一年后,我开始到处发问:为什么这里错过了截止日期?为什么这里没准备好?为什么这里不对,而这里却很好。
大学给了我管理方面的理论知识,而这对我有所帮助。我希望应用这些知识,但我感觉仅仅负责自己的工作,水平提升至一个艺术家是不够的,尽管我非常喜欢这样。我渴望承担团队工作的责任,为整个项目负责。
我的直接上司信任我,让我负责一个与图形外包相关的小游戏项目。一切就这样开始了。
之后你在 IT Territory 直接担任 PM,而不是作为艺术家。
是的,作为 PM 我稍早就开始了。在我离开 Kenjitsu 后,我被一家不太知名的公司聘用,那家公司同意让我担任 PM 职务,虽然我没有经验。在这一年中,我学到了很多东西,了解了完整游戏周期开发的基础和项目管理的基础。
一年后,另一家公司——IT Territory——决定在圣彼得堡成立一个分公司。新工作室的负责人是安德烈·米赫林 [现在是 Social Quantum 的制作人,——编辑注] 和谢尔盖·安德烈耶夫 [前 Nord 的导演,Mail.Ru Group 的游戏开发工作室,现在在 Social Quantum 工作,——编辑注]。他们几乎从零开始在圣彼得堡组建了这个分部,命名为 ITT Nord。
在我们见面之后,我去面试了,面试后他们邀请我在他们那里尝试管理开发工作。我当然欣然接受。该职位在一家雄心勃勃的公司,团队优秀有趣,我非常想在那工作。
当时对你来说,选择做什么工作有多重要?你刚提到你玩过 Doom 和 Quake,但在 IT Territory Nord,你做的是休闲类游戏。难道白天做一款游戏,晚上“为乐趣”跑去做别的游戏就不会觉得奇怪吗?
我不会掩饰,当时我完全是个新手,实力也比较弱。于是我得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,视其为提升专业技能的机会。当然,我所做的事情很重要,但在这个阶段我并未渴望加入那些从事硬核 AAA 开发的公司。

那时,例如,IT Territory Nord 还在进行像 “法奥尔” 的项目
是的,我一到家,就坐在电脑或控制台前,玩 Morrowind、Oblivion 和其他类似的游戏。
另一方面,虽然我在做什么游戏很重要,但在工作中我更关心其他方面。我希望我的每一个项目,抛开归属哪个领域,都能做到尽可能优秀和商业成功:“金钱能战胜邪恶”。
对休闲类游戏的喜爱是后来建立起来的吗?
我非常喜欢城市建筑类游戏。当社会网络和移动设备出现类似项目的时候,我非常高兴,因为 SimCity 2000 在我心中有个位置。偶尔玩 match-3 也很有趣,例如“时钟大师”。
没有对自己所做事情的热爱,可能也无法取得成功。因此可以说,从某种角度来看,我喜欢这个方向,因为我也为自己所做的内容而感到自豪。
我没记错的话,你是在 IT Territory 学习到免费游戏的知识的,对吗?
是的,但并不是一开始。工作室是朝休闲市场发展。你还记得当时 Big Fish Games 在处理高档独立项目的分销吗?我们起初就是在做类似的项目。休闲游戏。
对我而言,免费游戏的开始则是《龙》和《宇宙人》。不过在《龙》中的开发中,我并没有参与太多,主要是在建模和图形方面稍微帮助了一下。
IT Territory 的圣彼得堡办公室是后来开始深入涉足免费游戏的,致力于网络项目:“塔那特”、“法奥尔”,以及之后的休闲类“乡村农场”。不过到那时我已经离开公司,所以并未在 ITT Nord 深入接触这些类型的游戏。
你离开的原因是否与 IT Territory 加入 Astrum Online 有关?
没有任何关联。当我开始在 ITT 工作时,我认识了伊戈尔·马察纽克(Igor Matsanyuk) [IT Territory 的共同创始人,如今是 Game Insight 的执行董事,——编辑注]、阿丽萨·楚马钦科 [Game Insight 的创始人,如今负责初创公司 GOSU.AI,——编辑注]、弗拉基米尔·尼科尔斯基 [IT Territory 的共同创始人,如今是 Mail.Ru Group 的首席运营官,——编辑注] 和亚历山大·瓦申科 [曾在 IT Territory 担任 COO,后来在 Game Insight 担任总裁,——编辑注]。这些都是极具魅力的重要人物。总体而言,我非常喜欢 IT Territory 作为公司。
我认为他们发生的结构变化是一大进步。随着 Astrum 的加入,俄罗斯的游戏产业发生了变化。
这笔交易对我关于 ITT 高管团队的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。他们是第一批在俄罗斯游戏行业将其转变为大生意的人。这非常棒。
至于我从圣彼得堡分公司离职——并不是我自愿的,我被工作室的创始人解雇了。
不太意外。
现在我可以平静地谈论这一点,并幽默地看待这个情况,但当时我认为这种转变是宇宙的不公。总觉得“怎么会这样,我多棒,多优秀,拼命工作,却被请走”。
更重要的是,现在我觉得这是 ITT Nord 管理方面的绝对正确决策,甚至可能是迟来的。当时客观上我在领导游戏项目方面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。我经历了“过度科学化”和为了程序而进行的过程开发。最重要的——对产品的理解——是缺失的。
我设计了完美的层级结构,创建了所有开发过程的流程图,似乎一切运转正常,但实际效果却不是那么理想。一切都按照理论,但就是总是出现问题。
都有流程图,但结果却没有。
就是这样。我很快吸取了这个教训,并不再回到这种形式上。从那时起,我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官僚主义。这样的方式无法开发出游戏。
实际上,我选择离开,去做自己的事业。我一直想做自己的事情。
当时正是社交市场的高峰,社交网络的黄金时代:做你想做的事——一切都能成功(或几乎如此)。借此机会,我认识了两位非常优秀的合作伙伴,我们开始了业务,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。我指的是帕沙·苏达科夫和热院·萨夫罗诺夫。在那个时候,我们叫做 Bad Rabbit。之后,在我们分开后,工作室开始叫 Fairplay。我更愿意提及它作为 Fairplay。
他们来自一家动画工作室,有一些设备,电脑和人脉。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,开始工作,想出一些项目,寻找资金。
我们的主要平台是 VKontakte。当时我们发展迅速,最高时大约有 25 名开发者。我们搬去了市中心的一家好办公室,彼时正值又一次危机,圣彼得堡的租金大幅下降。我们尝试与各种出版商和投资者合作——包括专业投资者和非专业投资者。总之,和所有人都尝试过。有成功的项目,也有不成功的。
最成功的项目之一是“航空大亨”。我们做了一个项目,在游戏中,不仅可以建城市,还能建设机场。那个时候我们由 Mail.Ru 制作。来自他们的制作人是马克西姆·多斯基(Maxim Donskikh) [404 Road 工作室创始人,现在是 Game Insight 的总裁,——编辑注]。“航空大亨”是我们第一个真正成功的大项目。

“航空大亨”
也就是说,正是受到你们项目的启发,他才着手开发“机场城市”?
也许是的。毕竟我们并没有完美地实现所有内容,还有改进的空间。马克斯后来确实做得更好。
在 Mail.Ru 的第二位制片人是伟大的成本·伊宁(Kostya Iнин,这位也和多斯基一样,现今也在 Game Insight 工作,——编辑注)。马克西姆后来去 Game Insight 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,而我们继续与成本合作。
你能谈谈这款游戏在高峰期的盈利情况吗?
数字我不记得了,但我们给了 Mail.Ru 50% 或更多,而我们剩余的资金绰绰有余。我们同时还在开发另外两个雄心勃勃的项目。
发生了什么问题?你们发布了一个项目,又发布了其他几个,照理说应该持续下去。
我们选择了错误的策略。我们试图做太多项目。理应集中发展已有成功的项目。但恰恰相反,我们开始没有关注“航空大亨”。当时我们的想法是,如果一款游戏带来的收入是某个数额,那么五款《航空大亨》就应该带来五倍的收益。这是我们最大的错误:其他四个《航空大亨》都没有成功。
我们缺乏基于至少基本分析做出产品决策的理解。当时我们对市场营销一无所知,游戏宣传对我们而言十分陌生。我们真心认为,只需发布一款游戏,明天就会成为百万富翁。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误解,尤其在非专业投资者中,该误解更是普遍。
直到后来我们才明白,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。游戏需要支持、分析和推广。顺便说一句,有时确实可行,但非常罕见。
你在自己的工作室里犯了错误,同时重新学习。请告诉我,你为何再次接受培训?
新学习阶段是在 FairPlay 之前开始的。在 ITT Nord 工作时,我学习了很多。
我感觉我在项目管理方面的知识仍然不足。我不明白如何建设流程,如何对大量信息进行结构化,如何从数据中提炼出信息,保持专注。
如今有了 Scrum、Agile,以及所有这些流派。但当时什么都没有。然而有一个项目管理基础教育机构——国际项目管理协会(PMI)。它现在仍然存在,并成功发展。
当时在俄罗斯这是一个新鲜事物。我参加了他们的课程,差不多学习了两年。即是说,我完成了一门课程,再参加下一门。该机构的最高国际学位是 PMP(项目经理专业认证),获得这个认证非常困难,这被视为最高成就。但我全力以赴,虽然不是第一次,但第二次我就获得了这个学位。
顺便提一下,考试只有三次机会,第三次不合格就失去了机会。
这可能是我意识的第二次重大转变。我再次改变了看待世界的方式。
除了获得大量项目管理的理论知识外,我的第二次意识转变是:我学会了以结构化的方式看待事物和任务。准确地说,是以结构化的方式。我开始在项目中将所有东西归类,把握重点。我开始理解在大量信息中哪些数据是关键的,应该以何种次序排列。听起来简单,但如果把人们放在大量数据面前,绝大部分人会迷失,只有一小部分会找到关键内容,并正确排序。所有这些也让我更好地组织自己的时间,无论是工作还是个人的。时间是我们最宝贵、不可再生的资源。有效利用时间很重要。
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次突破,我开始以结构的思维来解决一些复杂的挑战。
你在 FairPlay 工作时学习吗?
是的,我在学习,但随着业务的开始,它开始占用我所有的空闲时间。
这是在 FairPlay 的第二年或第三年。你有自己的工作室,从理论上讲你很强。然而,为什么你选择去 Social Quantum,而不是继续发展自己的公司?
情况并非如此。我们的公司分裂了。热院去做营销生意,而我和帕莎继续做游戏。
那时我们面临深度停滞。我们不明白下一步该做什么,缺乏分析和营销支持。但我们有一支非常好的团队。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。因此,我们开始寻找合作伙伴,希望能帮助我们搭建基础设施,帮助制作新的成功游戏,并作为共同投资者。
正巧在一次 KRI 会议上,我认识了费佳·扎伊采夫 [Social Quantum 的开发总监,——编辑注] 和安德烈·特尔季茨基 [Social Quantum 的创始人,——编辑注] 。当时,他们正寻找能够在圣彼得堡组建开发“Megapolis”团队的人。我们达成了协议,他们将为我和帕莎的工作室进行投资,我们将帮助他们在圣彼得堡建立 Social Quantum 的分部。

“Megapolis”
你是从零开始建立 Social Quantum 的圣彼得堡办公室吗?
那里已经有一小队人,他们在圣彼得堡进行外包原型开发。安德烈·亚莫夫负责这一小队。我们就在这位老师的指导下在圣彼得堡建立了 Nord Quantum 工作室,开始积极招聘人才。
同时,我和帕莎的工作室在一段时间内也与 Social Quantum 共同开发项目。
也就是说,你在同时为两家公司工作?
是的。我们保持开放、合作的关系,我们是两家友好公司。我在两者之间都承担了角色。
在某个阶段,我们与 Social Quantum 的联合项目未能顺利进行。于是我们面临选择:要么完全融入 Social Quantum,要么继续做自己的事情。我们有一支优秀的 Unity 开发团队,因此决定继续制作自己的项目。
这时,马克斯·多斯基找到了我,提议在圣彼得堡创办 Game Insight 工作室。邀请我去莫斯科讨论。
我去见了马克斯,在 Game Insight 的摩尔中央办公室。所有 ITT 的高管都在——亚历山大·瓦申科、阿丽萨·楚马钦科、伊戈尔·马察纽克。我很高兴再次见到他们。同时,我还认识了一位非常有魅力的列昂尼德·西罗季金 [Like Games 工作室的创始人,曾在 Game Insight 担任首席制作人,现在是独立专家,——编辑注]。列昂尼德确实很厉害,给人以全身心投入的感觉。之前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的人。他可以在凌晨三点通过 Skype 回复工作上的问题,早上又出现在办公室。
最终,我们坐下来讨论。他们提出在圣彼得堡创办 Game Insight 工作室,但条件是我必须停止与 Social Quantum 及其他合作伙伴的一切联系,专注于 Game Insight 工作室。我同意了。
最初的提议是,你要做俄罗斯版的 XCOM?
没有,那个时候并没有具体的想法。我们只是坐下来握手达成协议。
我充满了激情、热情,想和这些人一起工作。我确定,与亚历山大·瓦申科、伊戈尔和列昂尼德一起,经过多次成功,我们会取得更大的成功。对此没有任何怀疑。
列昂尼德·西罗季金当时正在推进实验性项目。我们尝试了许多不同类型的项目,包括“宇宙游侠”的模拟游戏和跑酷游戏。
他也作为我们的总制作人。与他和亚历山大一起,我们讨论哪个项目先做。于是就有了开发手机 XCOM 的想法,采用免费游戏模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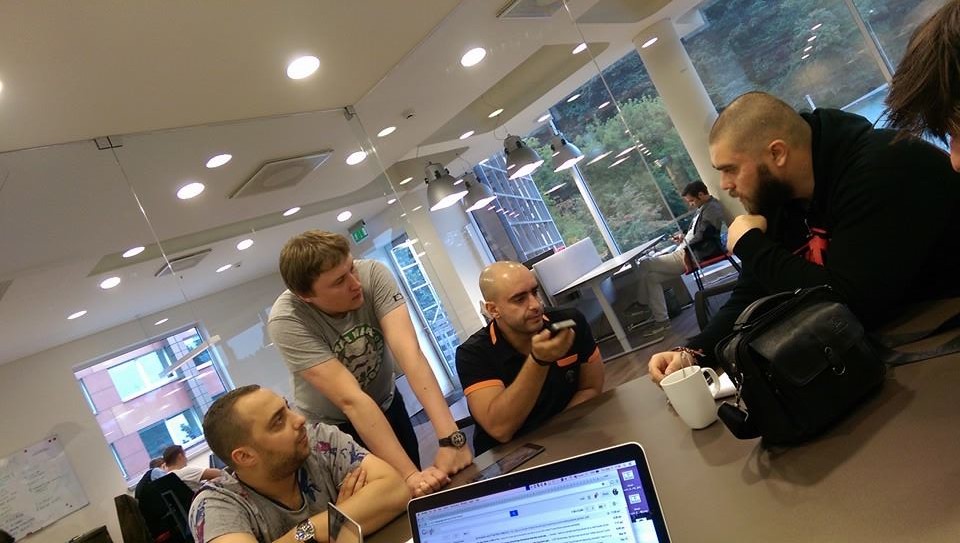
列昂尼德·西罗季金、阿纳托利·罗波托夫、亚历山大·瓦申科和亚历山大·博格丹诺夫
当然,不能称之为 XCOM,而应称之为科幻设定下的 TBS。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成了共识,以避免不必要的类比。
我对这个想法非常喜欢,因为我爱经典的 XCOM。无论是第一部、第二部,甚至第三部。我与这个类型非常契合。因此我们决定沿着这个想法前进。
那段时间非常好。我们正在进行创意开发,大家都被这个项目激励着。我们在做梦想中的游戏,至于我总是以热情怀念那个时光。我们的团队出色,项目出彩,前景十分诱人。
难道没有担心 TBS 必然会是很长的游戏时段,一小时?会觉得这根本不适合移动设备。
亚历山大和列昂尼德都是战略高手,他们建议试着做一些不那么实验性的作品。但团队和我都对手机的 TBS 想法感到兴奋。
最终成果如何?
在开发过程中,我们遇到了所有可能的障碍。关于 X-Mercs 的开发可以写一本《如何不开发游戏》的手册。我们在玩法上进行了复杂化,改变了技术,实现了更多的机制。与此同时,很重要的是,我们遵循了移动设备上游戏玩法的基本原则,比如游戏时长。
在积极开发前,列昂尼德找我说:好吧,伙伴们,游戏时长不应超过五到十分钟,不要三十分钟或一个小时的剧情。尽管有较短的游戏时段,但机制却相当复杂,游戏内的角色和参数,天赋也多。游戏难度相当高。
除了这些玩法复杂性之外,从技术角度,我们也是理想主义者。我们试图实施复杂的解决方案。“发射飞船”。例如,我们为了开发 UI 而选择了 scaleform,而不是易于理解的流行解决方案。在移动设备上,scaleform 运行得很糟糕,很耗内存。这导致我们不断返回重新设计。我们把 scaleform 删掉,转而使用 ngui,有无休止的更新 Unity 版本。我们从技术和玩法两方面对游戏进行了多次重大重构。

X-Mercs
你们什么时候意识到这款游戏不适合移动平台?
当我们推出软启动时。我们看到第一周的留存率很低,教程的转化率也不高。当然我们进行了优化,但依然能看到人们进入游戏后意识到自己玩了一个硬核 TBS,便离开了。
有一部分忠实受众留了下来,玩得很开心,但这远远不够,根本无法让项目获得经济上的成功。
有没有诱惑想放弃移动开发,改为适配 Steam?
这是一个存在的想法。这是在我们推出移动版的软启动后产生的。
但这个游戏最终并没有出现在 Steam 上。
巧合的是,在那时 Game Insight 进行了一次重组。当时推动公司发展的两个领导人——列昂尼德·西罗季金和亚历山大·瓦申科——离开了公司。让我感到失落。我习惯与他们共事。我感觉公司失去了发展方向,失去了共同目标。
还有一个问题。我并不清楚接下来等待我们团队和工作室的是什么。我们为 X-Mercs 进行了四年的开发,原本打算继续发展现有产品,并开发新的项目。但新的 Game Insight 管理层并没有给我们描绘出明确的前景和目标。
对我来说,缺乏目标是不可接受的。最终,由于我与团队对单一项目投入了太多精力,而这个项目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期待的成功,再加上缺乏前景和目标,我感到疲惫,决定离开公司。
而就这么没能开发出 Steam 版本?
是的,我们只开始了对 PC 的优化。
在和你交谈之前,我接触到了尤里·克拉西尔尼科夫 [Belka Games 业务发展总监],他表达了一个观点:这个项目被低估,并且超越了时代。你对此有何看法?
我认为这个项目非常出色。从技术角度我们做了一些之前没有人做到的事情,在移动平台上。我们和 Unity 也曾多次在其演示中被提及,在 Game World 的某一版中,他们几次称我们为最佳移动游戏。
也许这个项目确实被低估了,确实出现在了超越其时代的阶段。但我仍然认为,实验性项目——无论其规模多么庞大——始终是实验性的。我们应该早点启动。按照最初的计划,先做六个月到一年的原型,然后看看效果如何。
在这方面,我非常欣赏安德烈·普雅欣 [Kefir! 的创始人和 CEO,——编辑注] 的做法,他很出色。《Last Day on Earth》就是在几个月内完成的,并迅速上线。确认指标出色且良好扩展后,才开始打磨项目。
至于我们,当时我们几乎制作了一个经典的盒装版本。我们从开始到结束做了一个宏大的项目,带有完整的故事情节、历史背景和大量内容。
而我们当时其实应该逐步推进。
你感到疲惫,离开了公司,如果根据 LinkedIn 的简历来看,成了一名独立专家。之后发生了什么事?
是的,我在经历了四年的加班和没有假期后,确实感到很疲惫。
我告知新管理层希望辞职。大家对此反应良好,都说会考虑一下。过了一段时间,他们给我打电话,说准备启动辞职程序。
我计划休假六个月到一年,环游世界,看看所有地方:我自己什么也没见过,从未到过任何地方,只忙于工作。
我宣布辞职后,决定不让工作室留在圣彼得堡,而是将整个团队迁至莫斯科。我至今无法理解这个决策,可能我不知道某些情况。我原以为会在我离开后,另任一位领导人,让我们在 GI 的圣彼得堡工作室继续合作。我们甚至有这样的领导人,完全合适——谢尔盖·奥尔洛夫,当时是工作室的技术总监。他完全可以担任这个职位。
对于团队来说,迁移到莫斯科的前景显得非常奇怪。最终,没有人去,几乎整个团队也离开了 GI。
我感到对团队抱有责任感。他们为了我聚到一起,我曾承诺给他们光明的未来,而现在——呵——我离开工作室,拉开了公司内部分解的序幕。
简而言之,我开始帮助团队保持合伙关系。大家合作多年,没人愿意分开。休假也只好搁置。
那时,我和谢尔盖正好与伊戈尔和迪玛·布克曼 [Playrix 的创始人,——编辑注] 相识。他们想在圣彼得堡开设 Playrix 的分公司。最终整个开发团队和谢尔盖·奥尔洛夫一起加入了 Playrix。我的新生活阶段就此开始。
去年 11 月,你成为了 Belka Games 的首席执行官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团队。然而,为什么在开发过硬核游戏后你又回到了休闲游戏领域,这正是他们所专注的?难道不想继续做硬核吗?
不,我不想了。我完成了自己的梦想项目,花了四年时间。但当我走出办公室,坐上不属于我的 F-150 Raptor,而是更简单的车时,我问自己:“那么钱呢?”这使我个人的焦点急剧转向金融成功。

亚历山大驾驶着并非 F-150 Raptor 的车
对我和我的团队来说,现在有着非常高的财务动机。我们致力于发布商业成功的项目。而在与 Playrix 的合作中,我显著增强了自己在休闲产品上的专业知识。这不再是关于创意,而是关于商业和资金。
为什么选择 Belka?
Belka 的吸引之处在于,其创始人尤里·马赞尼克和迪米特里·胡萨彦愿意将公司利润分配给团队,甚至不是顶层管理者,而是所有成员。我认为这非常棒。
在这家公司,你可以获得真正的财务成功,对于团队和个人都是如此。没有其他公司提供类似的机会。此外,在 Belka Games,我的所有潜力、知识和技能都得到了充分利用——这太棒了!我终于感到自己被绝对需要。
这是主要原因,但也是有另一原因。我稍微厌倦了圣彼得堡,我在那儿住了超过 15 年,想尝试和家人移居其他地方。毕竟,持续的天气阴郁开始让我觉得不适。此外,我还觉得在这个城市我几乎已经做了所有事。
Belka 在明斯克,而我的母亲来自这里,我对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的联想只是温暖的。
请告诉我,今天的 Belka 是怎样的。人们知道它是行业的老将,但实际上这家公司只有一款游戏——“时钟大师”。
去年,正如迪米特里和尤里告诉我的,他们决定从根本上改变公司的发展战略。他们决定集中于长期目标,使开发更具专业性,这显然需要强大的团队和新流程的实施。目标是使 Belka Games 实现真正的成功,成为一家大公司。于是推出了新的战略——Belka Games 2.0。
今天公司正在引进顶级经理和部门负责人,他们肩负两个重大目标。第一个是组建一支强大的团队。
我们正在吸引具有强大专业知识的优秀人才。第二个目标是构建围绕开发的整个基础设施:分析、市场营销、QA、支持、社区管理等。而且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流程连接起来,使一切像一个有机体一样运转,而不创造过程只是为了过程。
这一切都为发布商业成功的产品所必需。这是我们的主要目标。我们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发布几个雄心勃勃的游戏,以使公司达到新的高度。
我们也看到了“时钟大师”巨大的发展潜力。我们正在积极推进该项目,几乎没有人看到过它。它的受众根本没有被耗尽。我们正在高质量地改善游戏,随着每个月的推移,游戏的表现越来越好。
我们深知,只有强大且有激励的团队才能创造真正成功的产品。因此,我们特别关注激励计划。我们相信,团队应直接参与他们所创造的游戏的财务成功。
现在可以说,在 Belka,我们建立了不依赖于任何人主观评估的奖金模型。
我们也致力于成为一家高科技公司,现在正在进行小规模的技术革命。

现在的 Belka
老团队对新变化的反应如何。从他们的角度出发,一切可能看起来是这样的:他们长时间开发了该项目,随后新高管和新成员加入,甚至他们还为一个过去五年没有参与的项目获得了奖金。
确实,这很复杂,存在特定的不理解,但我很幸运,团队非常优秀且团结。在很少的例外情况下,我们能够找到共同语言。因此在这方面并不存在太大困难。新流程的适应进展得很好,大家都理解这么做的意义,并且看到公司中的积极变化。
我努力建立一种基于共同决策而非直截了当管理的结构。这种方式非常有效,我对这种文化非常认同。因此,我们团队在各个层面上只做共同的决策。
你知道,现在Mail.Ru集团正在收购各家公司。你们现在也在考虑这样的潜在交易吗?
我们认为,公司的潜力甚至远未实现。现在出售公司没有什么意义。我们现在不考虑这个选项。但正如尤里·马赞尼克所说,我们是在做生意。如果明天有人愿意提出一个非常大的交易,为什么不呢?我们愿意考虑这样的可能性。不过,我认为现在还为时尚早。公司还没有推出我们前方的那些热门作品。
谢谢你的采访!
